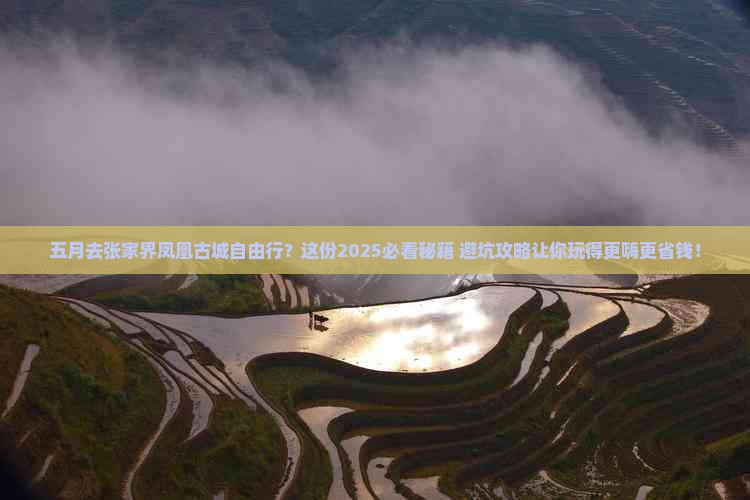03
建工行业如何转型法律人
LIJIANWEI STUDIO
我做仲裁员的时候,庭上有一方律师或法务上表现不错,庭后聊天,我就问你是法律专业的吗?他说不是,我是做工程的,但是确实在法务部,或者在工程部工作。我就感觉到,他们建工类公司的法务,不但懂法律,而且也非常懂专业。你在大型的、大中型的建设工程公司、房产开发企业工作,然后转过来做你们公司的法务,你的专业背景的确是一个天然的优势。
我鼓励你们这样的人去做法务,但是如何转法务呢?很简单,硬件只需要一个,参加律师资格考试,拿到法律职业证。当然法务也不要求有法律职业这个证书,但如果你自学法律学的不错的话,你在法庭展现出深厚的法律学养的话,我也是很佩服你的。但是现在我们为什么要拿一个学位,要考一个证,实际上就是一个象征,就是一个身份。一个非法律专业的人拿到这个证,就不需要向其他人解释,我是怎么学法律的,我的法律素养是相当可以的。那反过来,你就是清北人政、西政、华政等五院四系的这种毕业生,没拿到这个证,人家也怀疑你的法律学习水平。
但是我要讲的是,你无论是不是法律科班出身,要做法律工作的话,比方说公司法务,并不需要一定要通过律师资格。但是你有这个证,就是此处无言胜有言,你不需要对任何人解释了。
事实上,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要求,但是大中型企业做法务的,我也很少碰到没有拿到证的。你要表明你的法律素养,就必须拿到证,有这么一个深厚的工程行业的经验积累,再加上你考个证,这不非常好了吗。我接着讲第二点,你要想法律业务做得娴熟,做得好、做得优秀,其实你就主攻民商法就行了。民商法的重中之重就两个,《民法典》与《公司法》。两者一个是交易法、行为法,一个是组织法。但首先把第三编合同编搞清楚,换句话说,如果一定要简化我们的法律知识体系,或者强调这个专业的话,最后就两个法最重要,除了你专业做刑事刑辩、专业做行政诉讼的。包括知识产权的律师,这两个法也必须掌握,就是《合同法》与《公司法》,这是基础的基础,关键中的关键,支柱中的支柱。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突出自己的专业,给银行服务的搞好金融法;你做知识产权的,搞好知识产权,而知识产权有细分,专利、商标等等,截然不同。
总之,《合同法》和《公司法》是基础的基础。所以说,建设工程行业的人转法务,我觉得是一个高度值得赞同和鼓励、激励的一个想法。而且你的业务是蓝海,你无论是将来做律师业务,还是做仲裁是吧。第二要考个证,第三要把合同法和公司法学好,这是我的所有建议。
2024首场公司实务专场讲座
公司治理的制度细节
与公司章程设计实战
立即报名预约席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