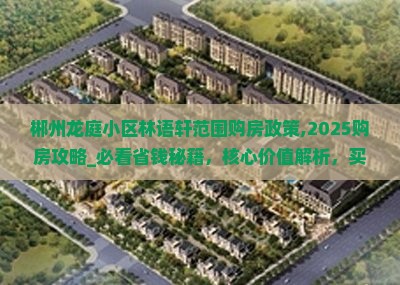张颂文、等主演的《》自开播以来,热度居高不下。凭借着紧凑的剧情节奏,以及环环相扣的探案过程,以及全员演技在线的表现,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。
随着剧情推进,会发现这部剧美女也不少,女配个个惊艳,作为女主的还真难压住。
表面上赵瓣儿是赵不尤妹妹,其实她和赵墨儿都是董其的儿女,赵不尤相当于帮好友养儿女,辛苦拉扯大,只是瞒着他们,当成亲兄妹一样,一家人打打闹闹但很和睦。
赵墨儿活泼直率胆子大,本来学医的,但当大夫坎坷,当仵作反而得心应手,天选法医。赵瓣儿甜美灵动满满少女感,梳着两个啾啾,总是笑意盈盈,像个小太阳一样活泼机灵,大大的眼睛,笑起来非常大方,神采飞扬明眸皓齿就是这样了吧!

扮演者出生于2001年,今年23岁。精致而深邃的五官,欧式大双眼皮,双眼又大又有神,鼻子很挺,嘴唇也饱满,典型的浓颜系美人。就是撞脸多位女星,像郭晓婷、、杨颖、杨雪和倪虹洁等等女星。


章七娘出现在帽妖案,她是目前最有反差感的一个角色,美艳动人的外表下,却有着一颗冷酷无情的心。疯批坏女人的演绎和《》李小冉扮演的长公主有得一拼。言行举止妩媚动人,却是最锋利的刀子,看不起贫苦大众说他们是蝼蚁,没想到自己最后死在蝼蚁手上。

有着强大的气场,嚣张的神情,把章七娘挥金如土、飞扬跋扈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。她一登场让人明白什么叫“珠圆玉润”的富贵宋朝美人!妆造完全复刻白沙宋墓中壁画里的人物形象,额间花钿,眼尾珍珠妆,头戴团冠,身穿大红色服饰,透露出雍容华贵,仪态万千,把张馨予的贵气衬托得满满的。

张馨予出生于1987年,今年37岁了,状态保持得很好。鹅蛋脸,桃花眼,下颌线清晰流畅,加上皮肤白皙透亮,很有光泽感,长相既清冷又美艳。中上庭较长,看起来就很有攻击力,属于睿智感美女。而且身材超好,高挑且凹凸有致,曲线分明,具有成熟女性的妩媚大气之美。


春熙一生凄惨,和青梅竹马爱人孙勃被迫分开,沦为章七娘家奴,还委身给她管家康潜,更是被随意打骂。这样的日子总出不了头,最后和孙勃联手杀死康潜,她再背后给了章七娘一刀再自杀撇清孙勃的关系,彻底解脱了。

春熙扮演者是陆妍淇,生于1992年,今年32岁。舞蹈出身,有着完美的身材和恬静安然的气质,在今年播出的《唐朝诡事录2》扮演清溪,纤腰热舞也出圈了。


池了了是樊楼花魁,出现在红绸飞尸案单元,登场时手抱琵琶,淡雅清新的模样我见犹怜,登台献唱苏词时更是美得让人心醉。独特的嗓音和灵动的表演,将池了了的才情与坚韧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出生于1994年,今年30岁。姜珮瑶这些年基本是女二专业户,而且演过杨紫、白鹿、周雨彤等人的闺蜜,也被称为“闺蜜专业户”。她的五官精致而不失柔和,眼睛大而明亮,仿佛能说话一般,脸型流畅,线条优美,即便是素颜也难掩其清新脱俗之美。

她长相融合了古典与现代的气息,展现出一种温婉与智慧并存的气质,许多角度都神似高圆圆。身材也非常有料,在《》中饰演的刮骨刀夏禾,就展现了性感的一面。以其英姿飒爽的形象和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


王云裳是开封府尹千金,骑着白马登场时酷飒非凡,能骑马能打架,英气十足,一副巾帼不让须眉的姿态。和周一围扮演的顾震有感情拉扯,体现了她大胆泼辣,刁蛮任性的一面。

出生于1992年,今年32岁,已经出道12年了。她的长相很英气,眼睛大而有神,直鼻微翘,嘴唇饱满,嘴角走势偏下,给人一种沉稳厚重的感觉。男装帅、女装美,游刃有余的穿梭于各种题材和不同类型的角色,可塑性很强。



王和扮演青年温悦,只在回忆中出现,是个清冷凄苦的刺客。一身淡青色衣衫,简单扎个丸子头,没任何发饰,散发着一种清纯淡雅的美丽,还有几分倔强感。


王和出生于2002年,今年22岁,演过《狗剩快跑》的白月光杏儿,得到了不少观众喜欢。王和流畅的鹅蛋脸,五官精致又柔和,笑起来两颊有深深的酒窝,山根上的一颗小黑痣,还有可爱的小虎牙。撞脸张雅钦、包上恩、陈妍希、刘浩存,柯佳嬿、张含韵、秀智等多位女星。



那么,你最喜欢谁呢?